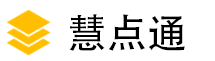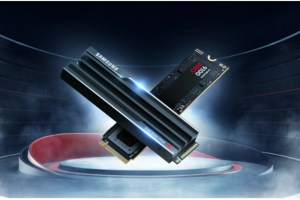——朱嘉明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人工智能:半个世纪的思想运动
——基于图灵机、MP模型和计算主义的历史考察
自1956年人工智能的概念被提出,人们不断地修正和补充它的内涵和外延。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为什么?因为人工智能既是科学,也是技术;既是信念,也是实验,具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性质,并且始终维系着“形而上”推动“形而下”,继而“形而下”反馈“形而上”的互动模式。在20世纪的科技历史上,与诸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样的纯科学比较,或者与更倾向实验科学的基因学比较,人工智能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互动的特征极为显著。
《易经》对此有过经典定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里的“道”,就是具有抽象特征的理念、观念、思想、哲学、逻辑,甚至是精神。至于“器”,则是具象的和具有物理形态的应用和实践。
人工智能是“道”在先,“器”在后。用哲学语言表述,人工智能的发展史很接近objective idealism(客观唯心主义或客观观念论)的原理:客观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物质世界,而不是相反。
本文主要通过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1954)、1936年图灵机和1950年“图灵测试”、MP模型(第一个神经元网络模型)以及计算主义的演变,探讨人工智能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演变特征,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思想运动。
一
图灵是人工智能核心思想的提出者。时间是89年前的1935年。那年初夏,图灵开始思考被后人称之为“图灵机”的“自动机器”,至1936年4月,图灵完成《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On Computable Numbers,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论文。从本质上说,图灵机是一种抽象的计算机模型,通过一个虚拟机器替代人类进行数学运算,也就是通过一个机器替代“计算者”,实现在任何可计算的范畴内的计算问题。图灵机对于人工智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因为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计算机科学的尽头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载体是计算机。
深入解析图灵机,其深层结构则是数学。而相关数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认知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的“可判定性”(Entscheidungsproblem)。可判定性是指一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某种算法在有限时间内得到解决。图灵对于可计算性问题,有双重立场:一方面,他证明了希尔伯特的判定性问题无解,另一方面,他将可计算性问题转化为一个直观可计算(有效可计算)的函数。
著名的“丘奇—图灵论题”(Church-Turing thesis),可以有几种表述方式:所有计算装置都与图灵机等价;人按照算法执行的计算和图灵机等价;人的智能和图灵机的能力等价。也就是说:“丘奇—图灵论题”,可以证明图灵机与可计算性的连接,证明图灵机可以实现某种算法在有限时间内得到解决。图灵机可以定义为一种计算的和模拟算法逻辑的数学模型。“图灵机的出现是对人类计算分析的结果,是一种编码”。
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最终还是要回答图灵机的第一推动力是什么?是决定论。
根据安德鲁·霍奇斯(Andrew Philip Hodges)撰写的《图灵传》:“显然,图灵机,与他早期对拉普拉斯决定论的一些思考,是有关系的。”图灵通过图灵机,“创作了他自己的决定论,在一个逻辑的框架中,来讨论思维是什么”。在创造图灵机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有点像超自然的东西”。图灵“证明了任何人类计算者的工作,都可以由机器做到”。图灵机在图灵那里,自始至终是存在神秘色彩的。
所以,到了1950年,图灵的《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问世。图灵在这篇人工智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文章中,一上来就提问:“机器能够思维吗?”为此要避免对“思维”有预设的定义。之后,图灵提出并阐述了“模仿游戏”(imitation game)的思想实验,即奠定了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图灵测试”。他“通过适当的增加存储和计算速度,并提供合适的编程,一个数字计算机可以表现得像人类么”?图灵对于未来机器充满信心,机器的发展会创造太多的出乎意料,学习机器可以在任何方面与人类的能力匹敌。而人们之所以不相信,“起因于哲学家和数学家们特别容易持有的一个谬见”。事实上,图灵的这篇文章更具有哲学意味,他在字里行间,已经将对机器可以思考作为了一种观念,赋予其一种基于科学论证的信仰。
无论如何,至少从1936年到1950年间的图灵是一以贯之的,他以形而上的模式持续其人工智能思考。这个时期,也正是“形而上”主导人工智能的关键历史阶段。
二
1943年,麦卡洛克(Warren Sturgis McCulloch)和皮茨(Walter Harry Pitts)共同发表了《神经活动内在概念的逻辑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一文,创造了麦卡洛克—匹兹模型(McCulloch-Pitts model),简称MP模型,这是第一次模仿生物神经元的树突、轴突、细胞核制作出了人工神经元模型。
MP模型的基础理论是“理论神经生理学”。该理论建立以如下的基本假定为前提:“神经系统上一个神经元网,每个神经元都有一个细胞体和一个轴突。它们的附属部分,或称突触,总是位于一个神经元的轴突和另一个神经元的细胞体之间。神经元任何时刻都有某个阀值,刺激必须超过这个值才能发起一个冲动”,“这个冲动从刺激点传播到神经元的所有部分”。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MP模型证明了:“一定类型的(可严格定义的)神经网络,原则上能够计算一定的逻辑函数。”
之所以MP模型在1943年产生了,首先因为生物学家麦卡洛克正处于开创神经生理学的前沿,深知神经元具有激发和不激发两种状态,神经元突触分为兴奋性和抑制性的两种状态,即“全或无法则”。所以,可以假设细胞脉冲对应于二进制的1或0的两种模式。当然,神经细胞响应输入的刺激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当时的麦卡洛克意识到,一系列神经元的活动或许可以用一系列逻辑命题来描述,他把这一系列的神经元成为‘神经网’”。为此,需要严格的逻辑术语。麦卡洛克需要得到数学家皮茨的参与。所以,在MP模型的深层逻辑,就是现代数理逻辑,可以看到罗素(William Russell)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深刻影响。
麦卡洛克和皮茨的工作最终验证,通过神经元表示的逻辑门实现计算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法。麦卡洛克和皮茨将生理学关于神经的研究带入数学领域,并与逻辑学相结合,开辟了实现机器智能需要回归神经科学或者大脑科学,成为当代神经网络中的奠基者。
值得强调的是,麦卡洛克和皮茨有着更大的企图心,他们认为,所有心智活动的关键方面,“都可以从目前的神经生理学严格推导出来”。皮茨明确提出:对于一个初始的随机的神经网络而言,“随着长时间对神经元阙值的调整,这种随机性会渐渐让位于有序性,而信息就涌现出来了”。
MP模型,也是人工智能历史上极为关键的“形而上”里程碑,至少在1956年的人工智能会议上,开始纳入人工智能思想、理论和技术体系。
1958年,心理学家弗兰克·罗森布拉特(Flank Rosenblatt)提出了感知机模型(罗森布拉特感知器),此感知器是根据MP模型的单层“神经网络”,是历史上首个根据样本数据学习形成正确权重参数的模型。这是MP模型从“形而上”向“形而下”转型的实例。
三
进入1980年代,从机器视角探讨人工智能的思想和技术选择与实验,已经相当普及和趋于成熟。但是,从人本身的认知和心理视角证明人工智能的普遍性,并未形成完整理论和技术支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计算主义得以兴起和发展。计算主义核心理念就是从物理世界、生命过程到人类的认知,都是“可计算的”。算法是一种存在,存在就是算法。人们之所以将“计算”和“主义”结合在一起,是因为计算主义不仅包含着科学,也包含了信念、价值观,甚至信仰的成分。
作为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泽农·W·派利夏恩(Zenon W.Pylyshyn),将计算主义系统化和理论化,推进了认知科学的进展。在人工智能的“形而上”思想演进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1984年出版的《计算与认知》(Computation and Cognition)是派利夏恩的代表作。
人们通常认为,计算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原子论,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主义。“万物皆数”是基石所在。派利夏恩在《计算与认知》的前言中,首先阐述了他的认知科学本质,“我考察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可以可能使人类(以及信息‘机器’人这个自然种类的其他成员)基于表征的行动变成他们在物理上例示这些表征的认知代码,而他们的行为如何可能变成执行这些代码的操作之因果后承。既然这正是计算机做的事情,那么我的提议就等于宣布:认知是一种计算”。“如果我们采取把认知和计算看作是同一属概念中的种概念的观点,就可以导出一个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结果”。
派利夏恩在《计算与认知》中的核心命题是:“计算是心理行为的实际模型而不仅仅是模拟。他引入了一个作为认知模型的计算概念,并进一步解释说,如果一个计算机方案可以视为认知的模式,那么这个方案就必须与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实际所做的方案对应。”在人的认知与计算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等同性,即所谓的“强等价”。强等价就是算法等价,体现计算模型与认知过程之间的相符性和对应性。
机器计算状态可以对应于一个等价的物理状态集合,也可以对应人的认知集合。所以,强等价性的实现要求计算模型满足严格的条件,以保证模型和认知过程在原则上是相似的。如果人类没有实现关于心理的计算,不能实现“强等价”,并不意味着动摇“认知是一种计算”,只能认为认知科学的发展尚不完善,没有达到物理学语言的表达层次。目前物理学可以提供描述物理世界的最普遍和最成功的概念。
在几乎以“认知是一种计算”作为公理的前提下,派利夏恩探讨了认知的“表征”层面,认知的可穿透性,从物理形态到符号的转化,心理表象和功能建构等。《计算与认知》的第九章题目是“结论:认知科学是关于什么的科学”。他的结论是:“认知科学的最终成功,如果它们成为现实,不得不解释各种各样的经验现象。它们将不得不与许多哲学讲和,并面对我们关于有意义的问题的前理论直觉。”也就是说,认知科学的建立,任重道远。
1985年,与派利夏恩在《计算与认知》的核心思想一致的多奇(Diana Deutsch),强化了“物理世界是可计算的”主张,“任何有限可实现的物理系统,总能被一台通用模拟机器以有限方式的操作完美地模拟”。多奇认为,算法或计算这样的纯粹抽象的数学概念本身完全是物理定律的体现,计算系统不外是自然定律的一个自然结果,而且通用计算机的概念很可能就是自然规律的内在要求。进一步推而广之,物理可计算主义的一个强硬命题是“宇宙是一台巨型计算机”。
在计算主义阵营中,数学家、逻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计算机应用开拓者勃克斯(Arthur Walter Burks)是重量级人物。勃克斯的代表作是《机器人与人类心智》,该书的核心思想是,“一切皆数”。“如果从外部给定其输入,在时间持续和空间广延上有限的任何自然过程,都能被数字计算机模拟并能满足对精确程度的任何指定要求”。
勃克斯的思想与其说有着来自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物性论》和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人是机器》的影响,不如说源于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思想。甚至可以认为,勃克斯也是莱布尼茨的信仰者,“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发现和推动的世界的实在性。因为它不难通过计算它一遍或通过验算加以证实。这就类似于算术中的九归验算一样”。为此需要引入诸如字母这样的符号系统,因为字母信息可以被数学化。
勃克斯坚定不移地认为:计算机和形而上学不是对立的,甚至意识、自由和道德,“在机器人中,也在人类中”。人的所有推理,包括发现和证实,都能通过“有穷决定论自动机”转化为数字运算,进而“实现人类的一切自然功能”。勃克斯提出一个假定:人们制造的计算机,不仅能归纳地证实经验陈述和推理,而且能通过选择适当的语言符号,演绎证明这些陈述和推理,那么,“这种计算机就构造了一个语言的经验应用方面的漂亮模型”。这不就是今天的以GPT(OpenAI公司开发的预训练语言模型)为代表的语言大模型吗?
一方面,人类心理和思想活动可以被计算;另一方面,计算机形成对人类心理和思想活动的计算能力。于是,人与机器人区别消失:人=机器人。
关于计算主义、心灵计算主义的批评意见从未间断。但是,计算主义无疑是人工智能历史中重要的“形而上”思潮。至今方兴未艾。
四
在20世纪的30年代至80年代,存在一个以“形而上”方式思考人工智能原理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涉及学科相当广泛,包括:数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等。不论他们各自的主要专业是什么,人工智能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视野。
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因为是师生关系和同学、同事关系,彼此相识。在学术领域中,他们相互启发、交流、争论和相互欣赏。著名的“图灵机”的称谓,是图灵老师丘奇(Alonzo Church)命名的;希尔伯特是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导师。
哥德尔和图灵的人工智能思想是有差异的,但是,哥德尔从来都肯定图灵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天才贡献。哥德尔认可图灵机捕捉到了“人作为计算机”(human computer)的直觉,并且把这个功劳都归功于图灵。之后在他不多的公开发声(文章或演讲)中多次力挺图灵,并且措辞几乎相同。哥德尔1946年为“普林斯顿大学200年”撰文中的一段话被最多提及:“他(图灵)第一次成功地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认识论概念的绝对定义,即一个不依赖于所选择的形式主义的定义。”哥德尔此处所说的“绝对”,是指图灵机不是相对的概念,它不需要依靠别的机制,它是最基本的装置。
麦卡洛克和皮茨的MP模型,为冯诺伊曼关于存储程序概念的二进制设计,提供了几乎唯一可以借鉴的技术思路。
不仅如此,他们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国极为有限的几个大学和机构:德国的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例如,在1930年代的剑桥大学,希尔伯特、罗素、维特根斯坦、丘奇、哥德尔、图灵同时在教书、研究和学习;在1950年代的普林斯顿校园,曾经也有过爱因斯坦、图灵、冯诺伊曼、哥德尔、纳什、麦卡锡同时在教书、研究和学习的时光。在1950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有过维纳、香农和皮茨共同研究的日子。
特别的是,对于这个群体,人工智能不仅是科学、实验科学和哲学,而且还是一种信念和理想。罗素说过:“尽管许多哲学家继续告诉我们人类何等灵秀,但我们的算术技能却不再成为他们称赞我们的理由。”香农这样回忆:“我们怀有梦想,图灵和我曾经讨论过完全模拟人脑的可能性,我们真的能够造出一个相当于甚至超过人脑的计算机吗?也许未来比现在更容易。我们都认为这在不久之后——10年或 15年之内——是可能实现的。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30年来都没有人这样做过。”
在20世纪,充满了不同的科技突破和革命,但是,这些突破和革命基本局限于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领域。唯有人工智能,引发了一个至少长达半个世纪的思想运动——一个包含融合思想、哲学、科学、精神与心灵的思想运动。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的形成和人工智能产业体系的形成,说到底,都是人工智能思想运动的“溢出效益”。更令人震撼的是,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的思想运动并未停止,在语言大模型的背后,依然是包含“形而上”基因的深度学习理论;在Sora(OpenAI公司开发的文本到视频生成模型)的背后,是关于人们可以模拟真实物理世界的执着信念。
今年的6月7日是图灵去世70周年纪念日。本文以图灵1950年在他的《计算机器与智能》的一句话结束:“我们或许期待着,有一天,机器能够在所有纯智能的领域中同人类竞争。”这一天确实在加速到来,甚至就在眼前。